民俗文化视野下的《牡丹亭》
陈劲松
《牡丹亭》中女主人公杜丽娘的死而复生,是贯穿全剧的重要情节。对于杜丽娘的复活,汤显祖在《牡丹亭记题词》中是这样诠释的:“天下女子有情宁有如杜丽娘者乎!”“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因此,杜丽娘之“情”堪称“至情”,像杜丽娘这样,用情达到极致的人,在剧中跨越阴阳两界,最终收获爱情。这就是汤显祖为《牡丹亭》故事情节的发展所预设的内在逻辑。
可是,杜丽娘“复活”的情节,在现代人看来,还是有些匪夷所思的。今天我们结合汤显祖的生平和相关民俗学的知识,对这个问题进行集中探讨。
汤显祖其人及其戏曲创作
2010年是汤显祖(1550—1616)诞辰460周年。汤显祖字义仍,号海若、海若士,别署清远道人,江西临川人。出身世家,年少颖悟,14岁即中秀才,21岁中举人,称得上名扬天下,春风得意。可是汤显祖的个性“孤傲疏狂”,性格决定命运,这冥冥中就注定了他终身仕途受阻的人生轨迹。汤显祖得罪了两个人,这两个人让他的仕途变得格外艰辛:一个是万历年间的内阁首辅张居正,另外一个则是张居正的继任者申时行。张居正久闻汤显祖之名望,欲将其招致门下,并希望他能与自己的儿子交好,汤显祖不为所动。
万历十八年(1590年),四十一岁的汤显祖将矛头直指时任首辅申时行,对其进行弹劾。后一年,又呈上《论科臣辅臣疏》,直陈朝廷失政,权贵弄奸。皇帝大怒,将他贬到广东徐闻县作典史,两年之后,又量移浙江遂昌知县。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汤显祖投劾罢归,不复出。世间之事往往祸福相倚,汤显祖罢官的经历,反而成全了他的传奇创作:《还魂记》写于1598年,《南柯记》写于1600年,他的最后一部传奇《邯郸记》,则写于1601年,再加上旧作《紫钗记》,合称《玉茗堂四梦》。明末文学家王思任,对这四部剧的精髓各用一个字来概括:“《邯郸》,仙也;《南柯》,佛也;《紫钗》,侠也;《牡丹亭》,情也。”日本汉学家青木正儿在《中国近世戏曲史》中,把同时代的汤显祖与莎士比亚并称为“东西曲坛伟人”,堪称是对汤显祖戏剧创作的至高赞誉。
以上就是汤显祖大致的人生和创作历程,像这样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他在进士及第时的排名仅为第211名,足可见当时的科举黑幕重重。科举之弊在汤显祖的《牡丹亭》里也有提及:陈最良,这位给杜丽娘做教习先生的,12岁即赴试,3年一次,竟考了15次,最终成了个腐儒,庸碌无为。这就是科举对个人生命的戕害。《牡丹亭》中,柳梦梅得中状元的情节,也具有很强的“无厘头”的意味,作者对此极尽嘲讽之能事。
汤显祖性格上的疏狂必然导致人生的多艰,命运的多舛,他把自己的人生经历放到了《牡丹亭》里,放到了他所写的各个人物里。所以剧中主要人物里或多或少都能觅到汤显祖的影子。巧的是,清代戏剧家洪昇也是年少成名,后来到了京城屡屡受挫,仕途上也没有什么大的作为。1688年,在三易其稿之后,最终完成了“曲中巨擘”《长生殿》的创作。个性决定人生,性格决定命运,所以汤显祖和洪昇的人生经历成就了他们的戏剧创作。
《牡丹亭》写于万历二十六年,汤显祖在遂昌弃官回家的三五个月内完成了这部杰作。徐朔方先生对于汤显祖此次弃官的动机作了如下描述:
汤显祖多年屈居小城知县,没有希望回到朝廷,才使他最后采取这样决绝的态度。这是气忿之余的抗议,不是从此消沉,自动退出政治舞台。有朝一夕时机成熟,他将重新出仕。当时的情况是这样,后来发生变化,谁也无法预料。
政治上的“重生”,恰恰是汤显祖期待已久的。循着这个思路再来看《题词》中的“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这个“情”也许并非男女之情那么简单。而杜丽娘的复活,是不是就隐喻着作者希望政治上的“重生”呢?
《牡丹亭》中的民俗意蕴
《牡丹亭》创作的主要故事来源,可参看《牡丹亭记题词》中所记:“传杜太守事者,仿佛晋武都守李仲文、广州守冯孝将儿女事,予稍为更而演之。至于杜守收拷柳生,亦如汉睢阳王收拷谈生也。”其实,《牡丹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故事来源,就是明代话本小说《杜丽娘慕色还魂》,但是这一点在《题词》里并没有提及。此外,还有学者认为,汤显祖的《牡丹亭》里有很多内容和他自己的人生经历有关。1591年他被贬为广东徐闻县典史的时候,经过大庾岭(位于江西与广东两省边境),1598年离开遂昌又经过大庾岭。而早在八百多年前的宋朝,《牡丹亭》故事的发生地大庾,确实曾有多个版本女魂恋人的传说故事,其中的一个还被宋代学者洪迈记载在他的作品中。洪迈所记故事与《杜丽娘慕色还魂》,以及汤显祖《牡丹亭》,在时间、人物、描写的中心内容方面,都有非常高度的相同和相似,此处限于篇幅不再展开。
第一个故事,武都太守李仲文丧女,年仅十八,葬于郡城之北。此后,一个姓张的郡守代替了他。张郡守之子年方二十,梦见一女,自称为前府君之女,两人遂行云雨之欢。后来李家在张公子床下发现了小姐的一只鞋,这只鞋是棺椁里的陪葬物,李家怀疑是他儿子把棺材打开了,张公子说明情况以后,两家一起把这个棺材打开。原来这个女子天天和张公子二人幽会,身体已经开始慢慢地复苏了,但是打开棺椁的时间太早了,最终还是没有能够复生。
第二个故事,东晋广州太守冯孝将的儿子冯马子,梦见一个女子。这个女子自称是北海太守徐元方之女,不幸为鬼所杀,请冯马子相救,并提出如果让自己复生的话,就嫁给冯马子。冯马子到这女子坟前祭拜,然后便打开棺椁。就见棺中女子完好如故。冯马子将其抱回家后悉心照料,一年以后,女子恢复如常。两人结为夫妻,生下二男一女。
最后一个故事说的是,汉时谈生年四十无妇,夜半读《诗经》“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然后有一个十五六岁女子前来与他结为夫妇。但是女方与谈生有约,约定三年之内不能以火照之。一般民间传说里都是女性提出要求,而违规的往往都是男性,日本传说里也有很多类似的情节。谈生晚上和该女子幽会,已经过了两年了,最后谈生不能忍了,以火照之,见女子腰下枯骨不复生肉,该女子也就不能复活了。这个女子赠一珠袍而别,珠袍、绣鞋在当时都是棺椁里的陪葬物。此袍后来为睢阳王家买去,王爷发现是亡女之袍。便抓谈生前来拷问,谈生以实相告,睢阳王认其为婿,两个人相拥而泣。
日本学者小南一郎认为,在这三则再生故事背后,存在过死去的年轻女子(恐怕还是未婚女子)通过其幽灵一度与世间男子交媾的方法则枯骨得以生肉而再生的信仰。杜丽娘与柳生“幽媾”,并告诉柳生实情,在石道姑及其侄子的帮助下,柳生开棺掘墓,杜丽娘得以复生,整个情节正是古老的再生信仰的体现。另外,以上三则再生故事还有一个相似点,那就是“女性把自己墓中的陪葬品,送给能使她复活的男子”。结合《牡丹亭》的剧情来考察,那所谓的陪葬品,应是指杜丽娘临死前画的那幅自画像。有了这样的一个再生信仰作为理论支撑,大家对于理解《牡丹亭》又进了一步,觉得杜丽娘的复生,并不是一个“情”字便能概括得了的,其中还有一个深厚的民俗积淀。
下面,我选择《牡丹亭》中富含民俗文化意蕴的几出剧目结合起来深入分析。第一出“劝农”,其主要人物是杜丽娘之父杜宝。有学者认为杜宝的原型就是汤显祖,剧中杜宝的政绩与汤显祖在遂昌任上的功绩遥相呼应;另一方面,杜宝对于剧中情节的发展,也是至为重要。杜丽娘死后进入酆都城,花神替杜丽娘求情,说杜丽娘阳寿未尽,她还和一个柳姓男子有一段姻缘。更重要的是,杜丽娘之父杜宝乃清官,这对于杜丽娘的死而复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劝农”一出之后,剧情便发展到杜丽娘“游园惊梦”,那么,这看似浑不搭界的两出戏之间,究竟有何内在的关联呢?如果我们用民俗学的眼光解读和分析的话,也许能够发现其中的奥妙所在。
“劝农”里有一句唱词“那桑荫下,按罗敷自有家,便秋胡怎认识他”。桑树的生长和人的性爱之间在原始人心目中是有因果关系的,人类学家詹姆斯·弗雷泽认为,在桑树底下行男女之事可以促进桑树的生长,所以罗敷女和秋胡的故事以桑林为背景,就平添了几许性爱的色彩。罗敷是采桑女,行人看到罗敷以后都傻了,因为她太漂亮了,因此,在桑林这样一个自然背景下,使君来调戏罗敷的行为,就有了一重民俗学层面上的意味。
再来看秋胡,他是鲁国大夫,秋胡戏妻的故事咱们都知道,最早出现在汉代刘向的《列女传》。鲁国大夫秋胡结婚没多久就当官去了,5年以后他回到自己的家乡,看到了一个女子,便上前调戏。那女子愤然拒绝。等到秋胡回到家以后一看,原来调戏的正是自家娘子,不由羞愧难当,而他的妻子也随即投水而死。汉代是一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时代,这个故事所体现的民间层面的内容太少了,秋胡妻子的死也许是注定的,因为只有她的死,才能体现出这个时代的忠孝节义,才能把贞节观“发扬光大”。
到了元代,有《秋胡戏妻》杂剧,在这部戏里,秋胡的妻子有名字了,叫罗玉梅。戏中,前面的情节都相同,罗玉梅和秋胡成亲,两个人没有相处很长时间,秋胡要去求取功名,回来了以后认不得他的妻子,便上前调戏。罗玉梅回来以后见到了自己的丈夫,羞愤难当。秋胡的母亲前来相劝,恰巧,当时在他们那个乡里有个人叫李大户也看中了玉梅,过来逼婚,在这样一个迫不得已的情况下,罗玉梅原谅了秋胡,两人重归于好。
所以桑荫、罗敷、秋胡这几个元素,都和性爱有关。但是这个男女性爱的背景和农耕背景联系在一起,男女间的性爱和农作物的生长有一定的对应关系,所以才会有后面的“杜柳欢会”。
再讲两个细节,秋胡离开朝廷回家看他妻子的那一天就是中国一个性放纵的日子——三月初三,就是女性求生、求偶、求子的日子,原始先民过“三月三”有男女裸浴的古俗,只不过到了汉代儒家思想控制了以后,正统史官把这些抹去了,只是巫官、民间的思维还是存在的。汤显祖是一个很了解史官,同时也很了解巫官文化的人,他在作品中已经透露出民俗信息了。
另外杜丽娘和柳梦梅合欢是在牡丹亭,牡丹是性爱之花。有句话叫“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杜丽娘偶发一梦,都是有很多细节呼应的,到最后这一刻梦见,可以说是水到渠成。因此,汤显祖笔下杜、柳“梦中幽欢”,其实质是以古老的农业祭祀信仰为基础,热闹的农耕场景和礼仪作为背景,以牡丹花为信物,花神为媒的一次欢会。男女间的欢会,与宇宙生命力的复苏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先民的原始信仰中,这一切背后的操纵者就是西王母。
还有就是《拾画·叫画》。柳梦梅拾到了杜丽娘的写真之后,便把这幅画挂在自己暂住地梅花馆里,然后整天“姐姐”、“姐姐”地叫,然后杜丽娘的游魂来了,见到柳梦梅自荐枕席,才有了之后“回生”的情节。她跟柳梦梅说了:我是鬼,不是人,你要把棺材打开把我给救了。柳梦梅胆子很小,杜丽娘下了场以后,再次上场就说:无论如何你一定要救我,我真的是感谢你,杜丽娘对这个爱真的是付出太多了。所以学者认为塑造的柳梦梅这个形象比较平庸,他在感情上实在没有太多的付出。
柳梦梅《拾画·叫画》,其蕴含的就是“画中人”的民俗文化意蕴。这类故事,大多以得到画为开始,其中男主角都很穷,要么是穷书生,要么是穷小子,他得到这幅画后,经过一番周折,最后与画中女子结为夫妇。
“画中人”民俗中还隐藏了“叫魂”的民俗事象。剧中,柳梦梅还真把杜丽娘的魂给叫来了,如果再将再生信仰的民俗积淀结合起来分析的话,杜丽娘的“复活”简直就是顺理成章了。
《牡丹亭》中的人物及其社会效应
下面,再简单为大家介绍一下剧中的主要人物,以及作品所引发的社会效应。
首先说的是杜丽娘。由于对杜丽娘这个人物的分析,学术界已经有太多的文章和论述,因此,我在这里另辟蹊径,从演员演出的体会出发,来分析这个人物。文本形象最终还是要通过演员的表演,在舞台上得以呈现。演员对角色的体会,也许比剧评家来得更为客观和公正。京剧大师梅兰芳曾演过折子戏《游园梦·惊梦》,他说如果是《牡丹亭》的时代,女子谈到自己的终身大事都会低着头羞答答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他们扮那个时代的女子,在她婚配的时候也想嫁个如意郎君,嘴里又不能说,只能在神情上把她的内心需要写出来,这是多么细致的课题。
另外再看一下日本人的表演体会,中日版《牡丹亭》请来了日本歌舞伎大师坂东玉三郎,他认为《牡丹亭》是很好的作品,能够在舞台上演出《牡丹亭》,对于他一个日本演员来说是一个挑战,而且是一个很高的荣誉。学术界有一个观点,就是认为剧中的杜宝,与作者汤显祖本人颇有几许相似之处,还有人认为柳梦梅身上也有汤显祖的影子。但是坂东玉三郎却认为,汤先生写这部戏的时候已经年迈,经历过时间沧桑,悟透人生。他笔下的杜丽娘虽然是个年轻的姑娘,但是在她病中,她发现自己一夜间相貌憔悴,于是想作画留住此刻的容颜。这些都不是一个年轻姑娘的心理,而是一个接近死亡的老者的心理。我在琢磨这个人物的时候,常常发现在人物背后,是汤显祖借杜丽娘发言。如果坂东玉三郎的推断是正确的话,那么杜丽娘的唱词“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付与断井颓垣”,便可以结合汤显祖自身的境遇来解读:它既可以看成一个绝代女子美丽无处安放的感伤之情,同时也可看作一个绝世天才空有一身才华,却在一个污浊尘世中的挣扎之痛。
坂东玉三郎说,《牡丹亭》最打动我的一点是男女在正常情况下无法相见相爱,只有在梦里或者隔着生死才能相爱。这与日本文化的某些元素不谋而合,日本能乐有梦幻能,现实能。中国的梦幻戏里做梦的人是主角,杜丽娘做梦梦见柳梦梅,杜丽娘是主角,她主动做的梦。但是在日本人的梦幻剧里跟梦搭配的那个动宾词是见,见梦,梦里的那个人才是主角,看的这个人不是主角。这就是中日文化有差异的地方,他说作品中大团圆的结局在日本文化中无论如何都不会出现。
杜丽娘身边的丫头名唤春香,通常人们会把这个人物和《西厢记》中的红娘作对比。然而,在人物塑造上,春香远没有红娘出彩,甚至可以说逊色了好多。譬如说,京剧《红娘》中红娘作为整部戏的主角,张生和崔莺莺倒沦为了配角。红娘的影响力如此之大,以后男女青年相爱,大家找媒人都叫红娘了。看来月老年纪大了,对于年轻人来说,吸引力也随之减少。试问你是愿意找一个老头来牵你婚姻的红线呢,还是会找一个善解人意、聪明伶俐,同时又漂亮乖巧的年轻女子,来作为你婚姻的引导者呢,我想,答案是不言而喻的。红娘形象符合中国老百姓共同的审美心理和文化取向。
说到春香,又要讲到汤显祖的故事了。有一天汤显祖失踪了,家里人到处找都找不到。那么他到哪儿去了呢?原来汤显祖写《牡丹亭》,写到杜丽娘还魂后见到春香陪同老夫人给她上坟,只一句“赏春香还是旧罗裙”,他自己便心如刀割,忍不住独去柴房,大声恸哭。足可见汤显祖在这个戏里倾注了太多的心血。一个作家和他的写作对象之间有这样深的感情,这个作品的成功也是可以预见的。
最后介绍的一个人物是杜丽娘的师傅,腐儒陈最良。
他为什么要去当杜家的教师爷呢?一个学了大半辈子儒学的人,满口仁义道德的人心里想的是什么?第一好说话;第二通官阶;第三勾结官府,赚取钱财;第四涂改考卷蒙混过关。到处吹嘘,我陈最良是谁呀,杜老爷家的教师爷,最后回到家里骗人。一个受过儒学教育满口仁义道德的人内心想的是这些肮脏玩意儿。真可谓“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明代儒学价值观的坍塌瓦解从这个人身上得到彻底体现。
《牡丹亭》里写的人物都是不完美的人物,要不就是生理上有缺憾,要不就是人生上有缺憾,要不就是道德观、价值观有缺陷。杜丽娘的爹杜宝是个清官,但是他不知道怎么样教育女儿。杜丽娘空有一身美貌,但是她碰不到自己的佳偶,任年华如流水般消逝。看着这么美丽的容貌随年华流逝,多么可怕,所以一定要留下一张写真,让世间人知道曾经有杜丽娘那么美貌的人存在,否则太不值了。剧中还有一个石道姑,生理上有缺陷,是个石女,包括柳梦梅也曾经打过秋风,拜谒过权贵,都是不完美的。
汤显祖《牡丹亭》写得那么好,自然引发了广泛的社会效应,也有很多轶事流传下来,颇有趣。“内江一女子,自矜财色,不轻许人。读《还魂》而悦之,径造西湖访焉,愿奉箕帚。汤若士以年老辞,女不信。一日,若士湖上宴客,见若士幡然一翁,佝偻扶杖而行。女叹曰:‘吾生平慕才,将托终身,今老丑若此,命也。’因投于水。”(《黎潇云语》)这说的是内江有个女子认为自己有财还有色,不轻易许人,后来因为《牡丹亭》,爱屋及乌爱上了汤显祖,汤显祖以年老推辞,那女子不信,说写《牡丹亭》的人肯定是风流才子,肯定不是你说的这样。汤显祖恨不得也学杜丽娘画幅画给她看。有一天那女子亲眼看到汤显祖佝偻身躯的模样,不由万念俱灰,投水而亡。当时的名伶商小伶,一日演《寻梦》,唱至:“阴雨梅天,守得个梅根相见”时,过于入戏,竟然气绝身亡。和《霸王别姬》那部电影中的程蝶衣一样,真个是为戏而生,为戏而亡,令人感叹唏嘘不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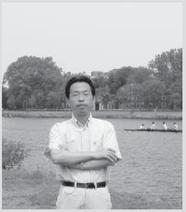
李晓杰
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
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政治地理研究室主任。1988年复旦大学历史系本科毕业后,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工作三年,任助理馆员。1996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获历史学博士学位。曾为美国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日本大阪大学COE研究员。主要从事历史政治地理、中国古代史及近代中外文化交流等方面的研究。论著有《东汉政区地理》、《体国经野——历代行政区划》、《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先秦卷》、《疆域与政区》等。